编辑:大众生活 来源:大众生活
![]()
原创 恨水墨客 双相躁郁世界

编辑、排版 / 龟龟爬 审阅 / Emile
The world has kissed my soul with its pain, asking for its returning songs.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泰戈尔《飞鸟集》
我已经挺久没有吃药了(小伙伴们不要学我)。从学校离开以后,我开始工作。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就医和报销精神类药物都是极为便利的,去就诊的时间也很好摆设。
工作之后就不一样。
我要包管每天都能定时起床,而且只能在周六日就诊。
我不能用我的医保,因为公司的医保报销要走发票。一年一签的合同制工作,我极有可能因为精神科就诊记录被辞退。
加上第一年工作的不定期出差以及不高的收入,医院的号得卡着点挂。
但是,双相的门诊又不是想挂就能挂的。即使挂上了,也不一定能挂到好的(Emile:或者说,适合自己的)。
急需复诊的时候,我可能会正好赶上昨天刚轮过门诊,于是还要再等一周。

我换过七八个医生。有的医生敷衍得令人愤怒,有的医生只是“么得感情”的开药机器。
第一次为我确诊的那位医生,在就诊结束后,鼓励我,告诉我说他也是双相。
医生说,他也经常感到无力,但仍要相信自己。
虽然我在病情的反复和一次次的涕泗横流中,忘记了他的姓名和面容,也不肯再去回忆第一次去精神科就诊的狼狈,但我仍然十分感谢他。

是我在打卡群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
是我丧失了坚持学业的勇气和能力,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依傍的借口?
是我既害怕别人知道,又厌弃自己的异样?
是背负了精神疾病之名,在看到新闻里犯罪的人用双相为自己开脱时飙升的愤怒,和心底弥漫的恐惧和脆弱?
是在工作中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一辈子就这样了?
是在进入一段恋情的时候,犹豫要不要告诉对方自己的病情?
还是在只身的时候就考虑我的基因或许不应延续,会不会给后代带去痛苦?

里边有一位贵州的双相女孩,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的法律系,但是因为双相住院了,情绪不大稳定。
她爸爸来看她时,她的状态很激动很躁动。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能安平静静地去和医生致歉,说会好好治疗,自己其时有点没控制住。
后来,她学校的两个领导老师来了。这孩子还会很礼貌地感谢他们。老师、医生和她爸爸坐在一起,聊她以后的读书问题。
接下来的那一段让我极为愤怒。
那个领导轻飘飘地说:“照她这个情况,就是稳定了也不适合继续读书,不如让她回你们老家当地,重新考个专科。出来随便在你们当地找个工作,随便赚个两三千块,也够一个人生活了,那样也方便你看着她。”
她爸爸有点惋惜和犹豫,觉得女儿考到好大学不容易。尽管学校也有学校的立场,可是他们根本不屑于去了解这个病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对其他同学造成危害,有没有什么步伐可以让她完成学业。
他们也没有去问她本人的意愿如何。
他们像驱赶蟑螂一样,把和普通人差别的刺头学生筛选并剔除出去,包管批量生产的一致性。

几乎是和她一模一样的经历,唯一差别的只是我并没有严重到需要住院。我也不会摔东西,没有暴力倾向。
但我最后也一样不可抑制地走到了放弃的地步。直到今天我,才敢去回顾和捋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在第一次坐在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只是被恋情失败、前男友高利贷追债拖累、加上结业论文没有头绪,导致的压力过大和情绪不稳定。
我去求助、预约,在签完保密协议之后,放心地倾诉。
一小时内,老师几乎没怎么说话。我有太多想说了,滔滔不绝地说,一刻不绝地哭。从原生家庭的偏心、来自母亲的容貌歧视,到恋情的不顺利、恋情导致的经济坏账,再到实习与结业论文难以兼容,论文没有能力写出来,感到自己急于改变而无力改变的焦虑。
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感到一丝轻松。在一个节奏紧张快速、大佬云集、学生优秀的院校,我因为不敷优秀产生的不安和脆弱,一直无处倾诉。
各人都很忙,各人都想要正能量。即使是朋友,如果无力慰藉你或无暇慰藉你,又害怕自己也陷进去,也会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或者因为不存在感同身受这件事,他们也不能完全理解。
我没有埋怨谁的意思。
我只是压抑太久,问题太多,无人可说,无处可说,也没有宁静的地方容我诉说,自己又无法消解。

但是,转折也来的很快。
辅导员给我打来了电话。这位只在开学和放假群里见过的老师,很快知道了我去找过心理辅导。而且跟我说,咨询师建议我去就医,让我下午马上去挂号看病。
挂了电话的第一时间,我非常愤怒。我签了保密协议的内容,辅导员全部知道了。而咨询师建议我就医,并不是第一时间通知我,反而是通过辅导员去向我施压。
不外,在一个个电话的敦促下,我还是去挂号了。
当天没有挂到号,第二天一早辅导员又来电话,并质疑我是不是不想去。语气中并没有关心,而是带着嫌弃和不耐烦。
挂到号的当天,我做了很多检查。我太累了,人生像出了一场车祸,过去两三年的失败、煎熬的恋情、家庭的反面睦,这些伤疤一次次被揭开,被我主动或被迫地一遍遍向各种人诉说。
在第一次就诊后,医生出了诊断。双相情感障碍,定向力(指一个人对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自身状态的认识能力)完整,不影响继续完成学业。
那一刻我似乎就被宣判了,其时只感到懵。

这个角色非常疯狂。他会在军队里开着飞机回来,会做很多激动的事,躁期性欲旺盛,急躁而蛮横,会搞砸自己的生活。
即使有逾越困境的智慧和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都因为他情绪的不稳定和偷偷不平药,所以一次次搞砸。
其时我很迷恋这个角色,是觉得他和他同性恋人米奇的恋爱很感人,是一种很朋克的浪漫:虽然你糟得要命,可那是因为你病了。我见过你最美最迷人的样子,也爱你绝望堕落的阴暗,并愿意陪你一起走过。
拿到诊断坐在安定医院的门口,我感到可笑。我和伊恩得了同一种病?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其时只知道,我病了?所以,我可以休息休息吗?我感到很累,想睡长长的一觉。
我和伊恩得了同一种病,但我未必有他的幸运。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不出口。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我真的很想死?没什么意义,也很搞笑。难道我能指望她理解吗?
我感觉虚无,没有什么值得我追求和留恋,我只是哭。
回去宿舍,我闷在被子还在哭,对面的舍友却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很快,舍友们都被叫去谈话。我一个人在宿舍睡觉,惴惴不安,梦里布满了难听逆耳的讽刺。
舍友们回来后气氛变得尴尬起来,她们都知道了。
那一刻,我羞耻得想要钻到床板里。我被迫接受着各人小心翼翼的关心,努力想体现得情绪正常,甚至主动讲一些段子告诉她们我没什么事,不会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宁静。

那时候各人都忙,结业论文的压力悬在头顶。另外两位当天下午有事,只有一位关系不错的舍友无奈地陪我过去了,一路无言。
或许陪着刚检查出精神病的舍友去看病也是很复杂的心情吧,无聊、紧张,肯定非常复杂。
在我进去看病的过程中,她定位了这家有名的精神科门诊医院,发了一句朋友圈,大意是“坐这儿我觉得我也抑郁了,人都有病”。
下边大波的同学评论,同门的学姐学长发来了很多关心,问她怎么了。
她没法说,只说没事没事,陪着同学来看病,她本人没事。
或许是我太脆弱敏感,拿着病历出来,看到那条朋友圈,感到一阵冷意。
我执拗地不想让很多人知道,究竟精神病是非常不被接受的,对普通人而言,可能是如同瘟疫一般的存在。她模糊的反应,让我感到一种被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恐慌。

在她眼里,或许一个精神病是做不了主的,应该由父母像小时候在幼儿园里肚子痛那样接回去。而我已经23岁了。
在她的坚持下,妈妈请了两天假来了学校。那阵子赶上她们单元工作改组,挺忙的,每个人一周有一天可以调休,请两天假意味着接下来的三周没有休息。
我很不肯意麻烦她,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的人生在17岁高考结束之后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我还是一个孩子,可以被照顾,偶尔可以提要求。
读大学以后,我就是一个瞬间长大的大人了。我必须理解父母,背负着要尽快长大分担家庭负担的期望。

我们在附近的肯德基吃早饭。路上妈妈一直在念叨,我怎么越大越不省心了,净捣乱,这下回去又一个月不消休息了。
到学校以后,宿舍有门禁进不去,我只好带妈妈去教学楼的沙发上等一会,自己去联系辅导员和院长。
妈妈很局促。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纱裙,坡跟的凉鞋,路上问我:“这个要不我一会还是抠掉吧,脚趾上指甲油脱得差不多了,还是不大好看,要让你们老师笑话了。”
我其时心里一阵悲惨。妈啊,你不知道,他们不是来找你谈话的,才没有人在意你的指甲油是否脱落。
他们是想让我离开。

因为之前我和妈沟通过,她没有松口。我学校定义的休学,不是只有人回去,而是连人带行李都打包带走。而这个三环内寸土寸金的地方,连宿舍都异常紧张。
我问过,休学半年回来,我还有地方住吗?还能住回我原本的宿舍吗?
答案是可能没有,到时候看学校的情况,如果实在没有,可能你得先自己租房,等有了给你摆设。
这意味着我可能回来以后的一年要租房住。在学校附近,一个床铺最自制一个月也要1500,加上日常开销,看病,这不是我们家庭能负担的。
而休学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回到老家去看病,报销手续也会非常繁杂。一个因为精神异常回家休养的孩子,会给父母带来不少困扰。我不能这样。
妈妈知道了这些,坚定地拒绝让我休学以后,辅导员就像换了一张脸,很愤怒地指责妈妈作为一个家长不负责任,也不为学校考虑,如果在学校失事怎么办?

妈妈没遇到过这种事。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她坐在办公室里给门外的我发微信,问我可以签吗?
我说:“签吧,否则你今天出不来的,辅导员不会让你不留下什么答应就走。”
签完之后,妈妈明显轻松了很多。吃过午饭,下午我带她去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我们去外边游玩了一天,就像以前她心情欠好来北京找我散心的时候那样,一切都似乎很美好。
但我也知道,一切都差别了。那时,我有着光明的未来,现在,我是一个被迫休学,前途未卜的人。
送妈妈上车走了以后,我坐地铁回学校。好了,现在我又是自己的监护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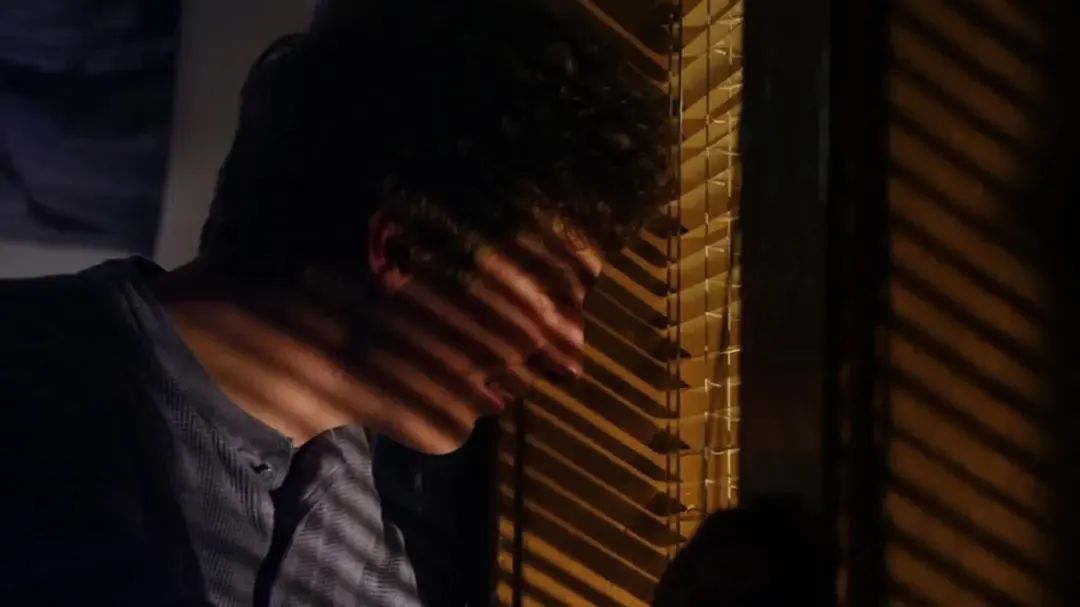
我偶尔兴奋地想,没那么大压力了,我吃得下睡得着,也不会暴饮暴食,我是不是已经好了。
我吃药没有严格遵医嘱。有时候,脑子里会想法奔涌,自信地觉得论文算什么,以我的才气,写篇论文出来真是易如反掌。同学们也并不比我优秀,看他们写的东西简直是一种折磨。
在兴奋过后,某天睁开眼,突如其来的恐慌和焦虑又会将我吞噬。我无法行动,躺在宿舍里度过漫长而煎熬的光阴,一天一餐,味同嚼蜡。
躁期买的运动衣、瑜伽垫到物流点了,可我不想出门,迟迟没有去取。我只想让自己缩得小一点,再小一点,直到消失不见。
舍友们在宿舍聊天的时候,我感觉她们的声音如此遥远。我甚至开始思考,我是否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感觉我在空气和人群中间的夹层里漂浮,我和其他人像生活在同一空间的两个世界。他们听不到我也看不到我,我就像鬼魅一般。

到我觉察到自己抑郁到出不了门的时候,我想求助,打开手机预约了医生,却又不敢去见。我只会一直痛哭,连宿舍的门也走不出去,直到错过时间。
每天我只下去拿一次外卖,让外卖员把外卖放在门口的石阶上走人,然后穿着睡衣火速跑下去拿走,不肯见到任何人。
哪怕只是看到电梯的数字变更也让我觉得烦躁、封闭、压抑、愤怒。
有一次去拿外卖,发现别人看我,我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回来的路上我才发现,自己的睡衣口袋里有一条跳出来的卫生纸,飘在外边。
我却对此毫无知觉,蓬头垢面,像一个勉强维持生命的机器,没有快乐和欢喜。那一刻,我觉得我似乎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品格。
我只能回忆到这里了,再往后,文字就太多了。每一句回忆,都让我像在刀尖上起舞,划得生疼。

我太天真了,我以为能力够了,去工作就能找到我想要的。但事实上我永远也绕不开没有拿到学历的问题。
在工作的路上,研究生肄业,甚至不如正常的本科结业生。人们会惋惜,会臆测,会怀疑,然后放弃你。
我有能力从事工作,但重要的核心工作会避开我。同样的工位,类似的工作强度,因学历的问题,工资缩水了三分之一,没有体例,没有一切福利报酬,像围观他人幸福的看客。
我一度接受了自己眼下的生活,感到一丝随遇而安的快乐,心境也随之稳定了一段时间。最近却又开始了入睡难,情绪不稳定的状态。
我会做很多很离奇的梦,风格和《爱,死亡和机器人》一样,只是角色都换成了家人、朋友、同事。他们有时候声嘶力竭,有时候面目狰狞,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我醒来之后经常沉醉其中良久,反应不外来。那种真实感,仿佛醒来的平凡生活才是梦境。

我已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又不肯就这样苟且偷生。长到25岁的人生,恍然如一场大梦。
我的心底很柔软,我爱很多人。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唯愿在乎我的人不必太伤心,爱我的人可以删除记忆。
固然我知道我不必害怕,这样的至暗时刻人人都会有。那天和好朋友聊起死亡,谈论了很多很深邃的内容,心里反倒更加平静,从容。
我想,我们的文化里是惧怕死亡的。能在活着的时候,从容不迫地谈论死亡,探讨生死的意义,那自己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